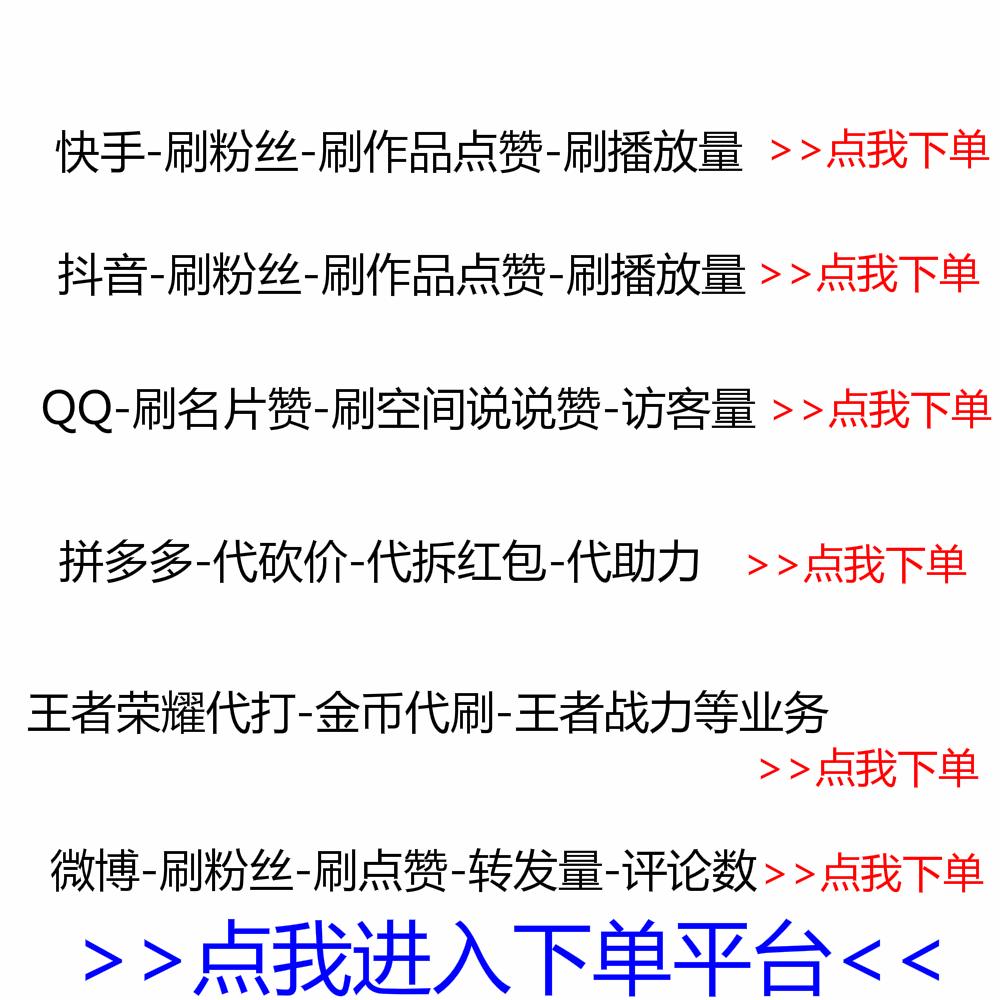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很少称赞他的团队,即使是创造了6亿日活跃用户的抖音。一位消息人士称,他听到的最令人鼓舞的评论是 抖音 团队“还不错”。
张一鸣以前不玩游戏,但在公司对游戏业务饥肠辘辘的时候,他立即做出了决定:每周五,他强迫自己玩游戏两个小时,时间准确到八点到八点。晚饭后十点。
旁观者惊讶地发现,在小型会议中,他的各种游戏派对专有名词从无知到熟悉。这被认为是自我迭代,“极度理性,像机器人一样理性”。那个人说。
在过去的四年里,这位酷酷但不带个人色彩的 CEO 一直是 抖音 算法世界的最高管理员。
在抖音(抖音海外版)与美国政府竞争的那一刻,我采访了近30位与抖音有着各种关系的人:现任和前任员工、经理、竞争对手、网红孵化器,网红,当然也是用户。
该产品在早期受到冷落。当他们度过黑暗的日子并为机器提供大量内容的燃料时,算法网络就会发挥作用。后来,它成长为一个大熔炉,吞噬了运营商、创作者和用户的大量时间。
根据第三方机构Aurora的数据,自2020年9月以来,抖音用户的日均使用时长为441.6亿分钟——近9万年。假设是一个人看的话,大概是需要让一个尼安德特人从远古时代用手机看到现在。
一、没人关心
2016 年秋天,字节跳动推出了一款名为 A.me 的产品。创始团队由不到十名年轻人组成。
这里的领导者是任立峰。他出生于1987年。他略显胖,留着小山羊胡,有时还留着大背。他曾在百度贴吧工作,但以前的同事对他印象不深。他喜欢竖起大拇指对别人说,“牛,牛。”
在2016年短视频方兴未艾的时候,A.me这个名字就是AB测试的结果。
他们设计了一个缓慢的标志——一个桃子音符躺在一个深黑色的底座上。为了吸引用户,他们举办了排名靠前的活动,但预算很紧。就算是人气最高的人才,奖励也只有一张50元的京东卡。
三个月后,A.me 更名为“抖音”。
刘朵加入时,抖音日活跃用户数只有40万。 “400,000字节算作产品吗?不是很好吗?!”打开抖音,刷十篇,出现的第11篇就是第一篇。
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只是因为他有同龄人,可以一起玩。
“当时短视频很无聊。 快手 比较大。我们觉得它应该是双栏的,所以我们应该点进去看。我们应该有一个封面来吸引注意力,我们应该有温暖的颜色。”在他的记忆中,把产品做成“冷色系,全面屏,不知道上面什么下面是什么软件”是出于“好玩又酷”。
在海外短视频平台Musical.ly上,流行一种叫做“技术流”的流行文化。参与者通过播放音乐和更换镜头来制作很酷的视频。这种形式在中国刚刚兴起。有一个叫“热猫”的应用,很多技术流的玩家都在上面。
薛老师是个狂热的粉丝,当时抖音团队认为自己做的产品,“薛老师这样的人都可以用”。
他们联系了当时在加拿大留学的 26 岁的薛老师。
薛老水告诉我,打着“中国版Musical.ly”的旗号的人很多,他们帮助抖音是因为,“他们更听话,说什么就变”;并且,抖音队里姑娘多,颜值高,活力四射。 “他们也懂表情包,你知道吗?这不是关于员工和员工的地位,只是我叫几个朋友和大家一起玩。”
老雪穿着一件碎花衬衫,一副复古的墨镜轻轻搭在鼻尖上。他对功能很挑剔,提出了无数的要求。最难满足音视频的不同步。如果他的嘴巴和声音的张开延迟了0.1秒,他就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仅这个细节就折磨了抖音一个月。
当时出现了另一个应用,新浪投资的小卡秀,它以假唱取得了黄金的开端。
他们也找到了薛老师,薛老师给他们写了一个版本的评论,首先是为了全屏。不过小卡修已经有了一定的体型,任何轻微的动作都会对平台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没有前进。
这些建议用在抖音,等到小卡修意识到《黄卡》上线时,已经晚了。 抖音借助技术流,实现了Musical.ly产品形态的像素级抄袭。
在改名A.me的时候,团队还取了一堆不靠谱的名字,比如“黄银”、“斗家”。据内部人士透露,选择“抖音”既是AB测试,也是高手计算出来的结果。
在Byte中,抖音只是众多实验项目中的一个边缘团队。此时的明星产品是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
由于工作站短缺,短视频从总部搬到一公里外的中国卫星通信大厦。 “百万日常活动不是什么大产品,只是为了好玩。”刘朵说。 “没有人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
当时的外部环境是:中国4G网络基本建成,流量资费下降,手机企业推出大屏智能手机,都为短视频的爆发提供了契机。以gif动画起家的快手,转型为短视频社区,无意踩风。
2016 年 6 月,在 A.me 上线前三个月,北京五道口发生了一件小事。在清华科技园最醒目的位置,快手取代了网易的巨大logo。
更让“宇宙中心”精英们瞠目结舌的是,这款讲述底层故事的产品发展迅猛,日活跃用户突破4000万。人们深深地意识到,短视频时代已经到来。
字节跳动孵化了两个短视频项目:火山视频和抖音,公司专注于火山。
“我们拿到的学分都是火山的残羹剩饭,比如四场跨年演唱会,其中三场是火山,还有一座火山真的是玩不下去了。他们说送给你抖音。”2017年底,抖音广告出现在浙江卫视跨年晚会上。
2016年,字节跳动仅有2000多人,估值数百亿。
张一鸣非常重视组织内信息的透明度和流动性。每两个月,在中航广场总部地下一层会议室,轮流召开产品商务会议,大家可以观摩。
“当我第一次使用 A.me 时,我什至不明白,我看到孩子们在那里跳舞,”2016 年 Byte 的一位中层人士说,“抖音我在那时。数据很差,各种测试,各种东西都起不来。”
二、创始七
抖音早期,员工每天中午会成群结队在办公室“吃鸡”。先玩《狂野行动》,后转战《和平精英》。有一次,其他同事觉得自己太吵了,打断了午休时间,被吹走了。
这群人没有太大的野心。最初的想法是做一个短视频社区,认为“做一个社区就够了”。他们是佛教徒,但意气风发,正因为如此,抖音聚集了一群热爱社区的人。
2017年8月,抖音线下派对巡演开始。
活动由运营牵头,负责人是李天,向任立峰汇报。她是一个 89 岁的女孩,有着一张娃娃脸。她喜欢穿连帽毛衣和工作服。她很小,但充满活力。这时候她让同事亲切地叫她“大田”,比“小田”还要嚣张。
上线前,新手操作很不安——创作者会不会相处融洽?商业间谍活动会溜走吗?
他们拿出了 1500 名应聘者,分析了性格,一一怪癖,并检查了其他平台帐户。从晚上 8:00 开始到第二天早上6:00,50人被选中。他们想确保场地“绝对干净”。
派对巡回赛听起来很贵,但一场演出只要5000元。
一个接近团队的人记得,窗帘是这场演出中最值钱的,几乎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这导致了为大师们准备了礼物,只有一顶蓝色的帽子,但“足以将一群人送上飞机”。
在成都的一个宴会厅,抖音ID终于出现了。他们大多是大学生,还有舞蹈老师、婚礼主持人……从事传统职业的人很少。
真性情是共同的特质,他们亲切地称对方为“摇友”。 “现在想想也太搞笑了,这群人一起玩,一起拍视频,一起吃喝。”创作者们被分成了六支战队。
对决规则为商场内拍摄,三小时后争夺流量,确定胜负。而获得这个荣誉的人,奖品只是一个火锅。 “如果你没有爱好,在这个地方你是没法相处的。”结束后,热情的年轻人喝了一夜酒。
晚会在北京开幕,抖音为薛老师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华语音乐短视频教父”。此时,他刚刚毕业回国。 “台上的产品经理一直在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薛老师说。
这个社区主要是年轻人,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挥霍。
“我想玩,我玩完了,我会带更多人玩,这不是飞轮效应吗?”薛老水招募了技术流的顶尖高手组建了TSG战队。他的观点是其他平台没有抓住本质。
“短视频平台只做视频吗?”他总结道,“抖音,这是一个玩具。”
金钱不是万能的。有竞品平台每月挖抖音人才2万到3万元,抖音只给几千块钱。在对方的怂恿下,高手们一小群逃走,但一般都无伤大雅。 “线下聚会,是为了维护区域人才的团结,你去就是叛徒,叛徒这群人,吐星子可以淹死他。”
很多受访者认为抖音的早期运营是其崛起的重要因素。任立峰有经营背景。由于他的卷发,他在内部被称为“卷发”。 “是娟娟带着李天,从一个市场到另一个市场,从名人到名人,和别人一起喝酒吃饭,照顾名人的情绪,他们早年做的事情就像打架一样。”字节跳动人说。
最早的七人组,除了任立峰和李天,还有两个产品经理,张博和姜凌安。张博辨识度很高,纹身的大花臂。其他都是运营,包括王嘉、玛莎、云云。
字节发表了一篇题为《抖音是如何形成的》的官方文章,讲述了创业的故事。不过这家公司对信息安全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本文中的成员都是化名。
此时,运营承担了扩大用户的责任。
他们到处挖人才——挖 快手、挖美拍、挖 Musical.ly、挖 YouTube、挖马蜂窝、挖 Keep。想一想就将其全部挖掘出来。挖完后,他温声问道:“你缺什么?心情好吗?拍视频了吗?”
他们公开去快手拉新用户,快手立刻注意到了封禁水印抖音。
几次之后,他们贿赂了快手的创作者,并在真人身上贴上了抖音的贴纸。 “快手也许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投票是这样的。”怀着求生的欲望,抖音换了方式放了几个月,耗资200万。
早期员工坚称,虽然抖音在产品上抄袭了Musical.ly,但内容生态建设非常规。
Musical.ly 有很多年轻的内容。他们判断它可以是年轻观众,但不能是年轻的创作者。社区应该包括食物、饮料和娱乐。
“我们将火山和快手定义为屠宰猪和牛的平台,我们应该更先进。”因此,他们寻找武术、健身、旅行、赛车、冲浪、葡萄酒、绘画、音乐、舞蹈、美容、烹饪……甚至航海——这些类别被细分,定义了 300 多个垂直标签。
配合《中国有嘻哈》开播,2017年下半年数据暴涨。抖音从小众亚文化到大众,从公司一角到中心舞池。
“我们针对的是一群有流行文化的年轻人,后续的内容爆发是化学反应,”一位目击者说,“当时我们联系了一些机构,问,你们的DAU是多少超过1000万。一问了好几个星期,就超过了2000万。我靠他们,他们都很惊讶。”但内心很平静。“我们只是每天拍一张照片,然后发给小组。 DAU 再次上升。这个很不错。我真的没什么感觉。真是佛。”
“基本上,我认为 抖音 的初始定位是错误的。”一位前中层高管表示,所有内容或社交产品都必须抢占文化制高点。 “一群有性吸引力的人”。
“人们更喜欢与比自己年轻的人建立联系。”就像Facebook在哈佛学生中流行起来一样,很多人都愿意和他们交朋友。涟漪随后传播到青少年,然后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
对比两个短视频应用,另一位中层人士认为,小火山视频是通过抓取快手的内容开始的,调子很难调整。 “抖音一点一点做,基因特别好。”
有点沾沾自喜抖音,2018年初遇到了麻烦。
春晚,抖音斥资3000多万元赞助浙江卫视。在最后一刻,我发现其中一个文件已经过期。
无奈之下,抖音把这个头衔给了刚收购公司的吉萌。 “原本,观众席上到处都是抖音,麦克风、口播、字幕。”电视台只能把相关词马赛克了,后期P变得精彩了。
春节过后,抖音DAU增至6000万,内部组织大团建。包括产品、运营、各种中台,已经从最初的个位数扩大到数百人。
不过,他们只是去了北京郊外的雁栖湖,吃了一顿简单的饭,就爬上了山。参与团队建设的最大领导是任立峰,整个过程并没有什么意外。 “我们一直是一个扁平的团队,”一位参与者回忆道。
目前,快手仍然是短视频的领头羊,日活跃用户超过1亿。 “没有人喊口号成为最大的短视频平台,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千年老二。”上面的人说。
三、中泰之手
前端只是战斗的一部分。站在潮流产品抖音背后,字节跳动依托“中间平台”运作。
可以想象,中间平台是一块积木,方便前端业务灵活调用。
一旦实验项目脱颖而出,更丰富的资源包括用户增长、推荐算法、技术、商业化、市场等,将以中台的形式注入。字节相信“强大的奇迹”。正规军全力出动,快速试错,快速验证。
2018 年初,抖音 刚刚达到一个临界点。
“早期的团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我要修正的是,抖音的成功离不开字节的大中台。”一位抖音的人认为Byte的核心能力有3个圈子:
高效的推荐算法,匹配人和信息;高效UG(User Growth,用户增长);有效的商业化。
“高效UG引入用户,使用高效推荐技术进行匹配,留存后商业化也高效。赚了钱再投资UG。”
他重申,抖音赢得最重要的是“字节在做”,有中期和综合能力支持。第二个原因包括:选择正确的方向;找准迹象后作出坚定正确的决定,将公司的力量投入到资源中;运营部分超越Musical.ly,成为潮流引领者。
“很多人认为字节是一家内容公司,这是错误的,”上述中层高管在 2016 年表示,“字节是一家 AI 算法公司。”
一位产品经理认为,抖音的推荐和提要流程过于强大,以至于产品无法提供与之相媲美的体验。 “我们把2018版本拿回去用了,留着也不会太差。”
基于这台强大的机器,初创公司员工将他们的工作描述为:“合适的人得到合适的原料。”
中段伸手抖音,前期团队慌了:今日头条会接盘吗?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自己想多了,抖音 保留了运营和产品人员。
如果把时间线拉到现在,你会发现即使发展成国家级应用,它的业务前端也只有400人左右,是一个“狭隘的抖音团队”并经营约300人。 , 数十种产品。放眼整个中泰,有很多抖音相关的人。
“其实全公司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做抖音和抖音”,一位接近抖音的消息人士说。
在张一鸣的带领下,字节对信息安全高度警惕,内部从不对外透露组织架构和职级:一是防止竞争对手研究挖人,二是避免因沟通障碍资历。员工身在其中就像是“盲人摸象”。
根据采访,我尽力整理出抖音与中国台湾联动的示意图。
bytes、UG中台和推荐算法中台四大中台,杨振元(副总裁)负责,洪定坤(副总裁)负责工程中台,张李东(中国区主席)负责商业化中期负责,他们都直接向张一鸣汇报。
市场部与互动娱乐部(IES)挂钩,由张楠负责,智颖负责。市场介入后,他主持了《抖音美丽美妙的夜晚》等大型活动,预算充足。
如今,Byte 的员工人数是 抖音 成立时的 30 倍,员工人数超过 60,000 人。也就是说,成千上万的员工都在为抖音努力工作。
四、灵魂是谁
字节跳动高管对新业务的态度各不相同。 抖音组织架构挂在张楠手下,但两名知情人士透露,“陈琳对早期产品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公司在火山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 “陈琳觉得抖音是一个全新的东西,Musical.ly是原创的。”他“总是很担心”并帮助招募人员。 ,派人。
在字节跳动中,张楠和陈琳是独立的高管。他们都出生于1980年代,有着相似的成长路径——字节收购其创业项目,跟随公司攻坚克难,开拓一片天地。张楠也向陈琳汇报了一段时间。
根据同事的评价,张楠是典型的运营营销人才,商业判断力强,产品能力略弱,符合抖音重运营轻产品的路径。
“她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也很有耐心和坚持,”一位中层人士说。字节不主张称她为“兄弟”或“姐姐”,而是在内部称她为“楠姐”。
张楠商业决策能力强,“是个很坚强的人”。一位员工回忆说:“我们经常讨论很久,她上去说:我不同意,下一个。”
知情人认为,张楠擅长单点突破,获得头部资源。比如,带领人偶变脸特效,罗永浩签约入驻。“头部的确立,必须集中精力。”
“有些团队判断工作是否成功,取决于张楠有没有点赞。”一位运营人员表示,张楠不关心细节,而是从全局和宏观出发。 “楠姐很犀利,她的观点很容易让人理解。”一位产品员工说。
作为一名女性高管,张楠被视为理想主义者,乐于在产品上培养兴趣。例如,领导了光面和剪裁的发展。员工认为女性高管可能会让 抖音 更加“甜蜜”。
细看抖音高层判断,任立峰的贡献在于他首先看准了方向,带领团队做前期工作;而张楠则善于动员和聚集资源——“公司可以在公司之外动员和想办法。杠杆”,在抖音的成长过程中拼命推动团队前进。
如今,凭借在抖音的成就,张楠从IES的负责人晋升为中国区CEO,同时也是抖音的总裁。陈琳调整负责教育等创新业务,出任高级副总裁。
在组织关系方面,任立峰向张楠汇报。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部流传着一个传说:“卷中有四个boss。”具体为:张一鸣、张楠、陈琳、张立东。这四人中,前三人已经介绍完毕,掌舵字节商业化的中国区董事长张立东。
“张楠是防守方,她负责抖音,其他人都是进攻方。”一位接近字节跳动的人告诉我。
这反映在商务会议中。比如张一鸣会问快手为什么做XX生意,为什么能做大;张立东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产品赚到源源不断的钱;陈林参与创作,直到专注于创新业务,才对抖音问的问题越来越少。
“在字节跳动做业务负责人很不舒服,你的老板、合伙人、和你不同的下属在各种会议上都diss,这就是字节跳动的作风。”上面的人说。
“字节的网络结构很累人。”上述产品员工表示,大部分公司使用树型系统,只需要向上级汇报,而网络意味着只要与其他业务有交集,他们就会分配你参加各种会议。 “你可以做一整天,也可以晚上开始工作。你每天工作,直到你衣冠不整。”
“说得不好,你得撕心裂肺,内心争吵。总会有人不断挑战你,不管他懂不懂。”上述运营人员表示,这是考验发起人的思维能力,并在混乱中争论不休。杀死一个生命力。
任立峰在 2019 年 6 月之前有四位老板。那时他迎来了一位新老板,Musical.ly 创始人朱军(Alex)。字节大手笔收购公司,调任抖音掌门人。
Alex 头发花白,产品能力强。他名义上向张楠汇报,但知情人却说张楠实际上退后了。
知情人透露,这背后是张一鸣的意愿。 “他信任 Alex,Alex 将 Musical.ly 从 0 带到了 1;他认为 抖音 的成功是因为 Byte 支持它并且有钱。”没想到,亚历克斯仅仅短暂执政了四个月,换帅宣告失败。
“这件事太复杂了,无法切入。”亚历克斯被调去接管抖音,张楠回来了。 抖音 又回到了她的手中。
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 “可能是张一鸣安排的。”另一位前中层高管表示,让亚历克斯先在国内实习,然后再出国。反正国内的系统已经很成熟了。 “老板不会把他所有的意图都告诉你的。”
基于中期和网状治理,字节跳动提倡集体决策,不依赖个人。 “每个人都有一个认知盲点,要等有人把盲点揭开,产品才会遇到瓶颈。”一个在抖音工作了三年的员工觉得这很性感。
抖音的灵魂是谁?有人说是任立峰,有人说是张楠,甚至有人说是朱军(因为抖音的产品形式来自Musical.ly)。
据上述知情人透露:“张楠不认为他能做到,一鸣也不认为张楠能做到,他认为自己已经赶上了这个时代。”在这场灵魂之战中,更多的人投票给了张一鸣。
虽然张一鸣从未在前线指挥过,但他们相信抖音成功就是系统的胜利。
它带来了一个冰冷的现实:抖音也许根本不需要灵魂人物。在这个理性至上的公司里,除了张一鸣,没有人是绝对重要的。
“这个螺丝没了,可以换另一个螺丝。”上述操作人员表示,“不是说这台机器的轴承特别大。”
五、电源变化继电器
在抖音,您会遇到性格丰富的同事。有的纹身,染发,有的玩跑车,极限运动,有的喜欢穿花哨的衣服——上身西装,下身短裤,一双亮色长袜。
“我对我们拥有的美女数量感到震惊,”一位男性员工高兴地告诉我。但你也会发现这里的周转率很高。年轻人一个接一个,一个笑话是:“一个月是老员工。”
他们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感觉,“积木”是一个恰当的比喻。 “等你建好,地方就稳定了,你就可以撤了。”
初创员工有深刻的理解。 “每个人都在交接棒。”在他看来,这是一场接力赛,而不是一万米跑。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业务阶段。像他这样的老员工陆续接手了三四家新业务,都是从0到1,然后“一一交接”。 “第一次会比较难受,以后会缓解的,没人觉得你应该坚持。”
从一开始,音乐就是抖音的灵魂。第一个音乐负责人叫朱杰,毕业于歌剧专业。朱杰最初负责今日头条音乐,后来带领团队落户抖音,建设音乐中心。她向任立峰汇报,然后迎来了抖音从神曲中源源不断的2018年。
在像音乐这样的情感项目中,有一段时间内在的尴尬。 “公司所有的业务都是用数据量化的。”一位音乐中台员工表示,他们无法通过“音乐打动人心”进行交流。幸运的是,团队用数字证明了自己。
2018年中国百强选手中有70%来自抖音。
然而,就在成就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苦涩。次年年初,公司招聘了一位新的音乐总监穆飞,担任朱洁的职务。两人尝试合作半年,新负责人主要开发MV。
但大环境是唱片公司不再投资MV,产能下降,业务天花板明显。两人没有共识,故事以朱洁的离开而告终。
空降兵往往是“交接”和“换帅”的前奏。故事还没有结束。 In 2020, Mu Fei will leave office and Cao Zhen will take over.
If the business is in trouble, the handover will happen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For 抖音 in 2018-2019, “content generalization” is a long-lasting battle, and it is also a must for the mass entertainment platform. In most categories, 抖音 has planted the red flag of victory. But it also has its moments of missteps.
Frustration comes from greed for local life. In mid-2018, at the Shanghai headquarters in Caohejing, 抖音 secretly established a POI (Point of Interest) team. They assembled thirty people, which was a luxurious lineup for the 抖音 at the time. The team only accounts for one-third of all operations staff expanded to 100 people.
Relying on the POI details page, these people operate two vertical categories of food and travel. They want to do everything they can to steal a piece of fat from Meituan’s mouth – but blows follow.
People close to the project said that at the earliest they built their own product functions and hoped to close the transaction loop by themselves. Merchants settled in the background through the enterprise account and launched coupons on 抖音, but it was too difficult to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of the industry chain. So they turned to third-party services, such as food delivery and group buying platforms, and travel and hotel B2B platforms, but there was still no improvement.
On the one hand, the traffic loss is large, “less than 1% of the actual POI details p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er’s mind has not been developed”. To make matters worse, management was ambiguous on key issues. Content and transactions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n local life. Regarding the priority of the two, “OKR has always been misaligned.”
抖音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rebuilding Meituan. A core person pointed out the lower-level logic: POI is the logic of planting grass, mainly based on active demand, and 抖音 is based on massive recommendation distribution. “A coffee shop can only serve a radius of five kilometers, such as 10,000 people, but 抖音will be distributed to 100 million people.”
Another person sai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cal living and information matching is:
There are geo-restrictions; inventory is divided by time, e.g. hotel inventory tonight will not be available for tomorrow night.
There is also controversy at the top about whether POI should be done and how big it should be.
In just two years,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POI changed like a revolving door — first Zheng Wei, then Xiao Rui, and then Tang Yunying.
This year, the POI reporting relationship has shifted from Li Tian to Lu You. He just arrived last year and led a team in Shanghai to do 抖音 on-site social networking. Lu You reported directly to Zhang Nan, and part of his responsibility was to lead the POI team to transform into social networking in the same city.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insiders rushed to make POIs, and the team increased to about 40 people when it was prosperous. But under the continuous tossing, nearly half of it has been los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company as fast as ByteDance.” The above-mentioned old employees sighed.
“It makes everyone feel like they have been beaten with blood. They feel uncomfortable, boring, and boring with money and waiting for promotion.” Take the start-up operation employee as an example. Except for Li Tian, who is firmly in charge of the operation, the rest Everyone is no longer in the company.
Another example: Advertising and e-commerce are all started by the 抖音 team, and then handed over to the commercial middle office, and many transition teams have left. “I feel like getting off the bus at the point of time in 抖音, I didn’t try to protect the country in the end.”
Parting is hasty. Many people have non-compete agreements tied to them, and they can only be vague about where they came from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
2018 was a pivotal year for fighting spirit and turning the tide of the war. 抖音Experienced crazy growth, and the daily active users exceeded 200 millio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surpassing 快手. Behind this is the rapid handover and expansion of the baton. The Zhongweitong Building was soon unable to sit down, and the team moved to the larger Zijin Building.
The warmth fades away. Early employees felt the most obvious, and since mid-year, 抖音 is no longer a content community. In the past, 抖音Daren had WeChat for each other, and “suddenly I felt that there was no circle for Daren anymor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company generously distributed year-end bonuses to 抖音 employees. According to rumors, Ren Lifeng was paid 100 months’ salary, and other early employees were about more than 20 months. “Two years in 抖音 is really like ten years.” Under pressure, some employees gain weight twice as fast.
抖音Culture is known for being fast, and everything is fast-forwarded at 3.0x speed.
Xiang Mi joined the job, called for an interview in the morning, and sent an offer in the afternoon; it was too late to reserve a conference room, so a “stand-up meeting” was held every morning; OKR was reviewed every two months, and the goal was radical, and he had to be tight at all times to drive himself forward run.
Here, it is especially rude to receive a message “read but not replied”, and the other party will pull your leader into the group after a while; the promotion plan is also, the product review will be held in the same week, the AB test will be launched in the same week, and the system will be released in two weeks. We analyzed and analyzed loopholes from data, R&D, and algorithm aspects, quickly pulled resources from China and Taiwan, and completed the launch in one month.
In addition, they have big and small weeks that can’t be beaten – every other week.
“Bytes has always been a ‘survive’ culture, and when you don’t get results every two months, you are likely to be killed,” said an executive close to 抖音, “Yes I am anxious every day, and the frequency is particularly intensive.
Have a meeting every minute of the day, start answering emails at 7pm, and deal with trivial matters. The boss wants to report to you at 12 o’clock, and is waiting for your stuff at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
“On this big ship, everyone was under high tension. We were trained like machines for three years. There were no friends, no emotions, and no interaction.” A middle-level recalled, huge Under pressure, he became sharp.
“It’s so fast, I’m almost crazy, talking so fast, I think everyone is an idiot, and I’ve even been yelling at people all the time.”
It was Ren Lifeng who made the climax of the battle, even if he founded 抖音, he was not spared. In 2020, Byte announced that Ren Lifeng would be transferred to Xigua Video.
This company has a strong system, and because of this, no one can match the system. People are even like “parts” in the system.
People close to ByteDance said that ByteDance has rotated the middle-level staff for one round from last year to this year. “Huanjuan went to Watermelon, Zhang Nan (male) went to Feishu, Han Shangyou went to 直播, basically all the names we could count have changed.” The company lacks a little human touch.
He knew a middle-level leader, and when he wanted to give him the airborne leadership, it was only three days from the announcement to the announcement, “there is no prelude.”
A number of employees interviewed said that he was transferred to Lifeng because of the challenges of making watermelon videos, and the company gave him the opportunity to prove himself again.
“It’s too official,” said the middle-level above when I paraphrase, “it’s a secret that can’t be told.”
Another抖音person said that the 抖音team is strong, but also has a politicized vibe. “You can read the air.” But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concentra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many companies outside.
抖音Growed into the mainstay of the company, transitioning from making a big cake to a cake-sharing stage. Many relevant people have reported that politicization and mutual tearing have emerged internally. “This is the price you have to pay for a first-tier product,” said a grassroots employee.
Tencent News “Periscope” learned that in September 2020, 抖音 ushered in a new head of product operations.
The internal system shows that the name is Seven and reports to Zhang Nan. A former colleague revealed that she was a strong post-80s female manager who took over Ren Lifeng’s position. 抖音Operations, products, and community safety all reported to her. For airborne executives, flexibly deploying the building blocks and the people behind them is a challenge and a required cours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middle and senior management of ByteDance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responsible persons”, the positions are ambiguous, and the reporting relationship is also changing.
“这家公司就像地铁,所有人挤进去,车开了,呼一下又出来。”上述中层说,很多人都是忽然来了、忽然走了。“它就是那样激进。”
六、抖音没有头号玩家
公司内人员疾速轮替的同时;在窗外更广袤土地上,抖音正以最高速度吞吐网红。
“大多数抖音网红生命周期就半年,甚至只有两三个月,这是很残酷的事。”一位MCN(网红孵化机构)CEO说。
“好嗨呦,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2018年10月,待业在家的余兆和录视频,讽刺蹦迪很装,没想到爆火。
“那个流量咔咔往上涨,一晚上涨粉几十万,每天都很疯狂。”他更换抖音名为“多余和毛毛姐”。凭借男扮女装和无厘头表演,不到两个月粉丝破千万。
之后的2019年,毛毛姐为代表的剧情号独领风骚。几乎无人不识毛毛姐。 “我那个时候流量好到什么地步?讲一句话就一百万的赞。”毛毛姐告诉我。他从老家奔赴上海,成为裹挟进时代飓风里的人。
不仅荣获“现象级网红”称号,还成为娱乐圈座上宾——《武林外传》里饰演邢捕头的范明说,你和姚晨表演异曲同工,很松弛;活动上,赵薇拿话筒当众cue毛毛姐。
“微信好友名单会有汤唯,太吓人了。”突如其来的荣耀,让他受宠若惊。
这是掘金抖音流量的黄金时代。在广州,1992年出生的白水头一回当老板,就尝到暴富快感。
“简直像是奇迹。”白水刚毕业找了份月薪3800元的工作,摸爬滚打四年,去年是转折点,领导派她成立MCN。“我们从投入到变现只花了十万块钱,指定是没有人信的。”
2019年6月,白水公司风楼传媒孵化“黄三斤”。“第一条就爆,三个月粉丝就一千万了。”初出茅庐的公司营收过千万。“我们踩在风口上,真的有很大是运气。”
快手生态偏自然生长,野生达人多。 抖音不然,从2018年就MCN化、工会化,一层一层建生态。
对流量敏锐的生意人蜂拥而至,2018年是起点,2019年达到火热,MCN激增至两万家,他们分布在北上广深、成都、长沙等地。
业务采取两种模式——孵化型和签约型,前者培养素人,网红分红比例小,10%左右;后者签约已有名气的达人,如毛毛姐签了无忧传媒,网红分成高。
网红月薪是底薪+提成,不少可达六位数。
像“毛毛姐”、“黄三斤”这样的剧情号,是2019年抖音最大风口。
MCN批量生产,他们采取“编导责任制”,对签约达人的演技和人格魅力要求颇高。为便于管理,有些MCN要求创作者打卡上班。公司会和他们签严格的“全约”(全平台经济协议),社交账号、线下演出等全交予公司管理。
一旦违约,便向其索要高达五百万赔偿。然而可怕的是,今年疫情后,该品类流量陡然下滑。
“客户更审慎了”白水说,剧情粉丝规模虽大,但ROI(投资回报率)低。“一抓一大把两三百万粉丝的,都不值钱。”
2020年,MCN不约而同大批裁撤剧情号。 “那些老板说停就停,都不考虑卖号,没有人会接手的。”而今年的趋势是,剧情号对IP和差异性要求高,真实且接地气的号起量快。
“没有安全感”是创作者共有感受。 抖音是公域流量,内容投进种子流量池,数据指标越优异,算法就把内容送往更大流量池,层层通关。
只要单条内容挑动不了用户神经,粉丝再多也无济于事。 “你要时时刻刻带来新鲜感。”五月美妆CEO五月说,算法机制逼着创作者迭代,“你会一直一直非常崩溃,很累”。
我走访了位于北京、广州、上海的七家MCN发现,所谓“短视频思维”就是“怎么拍出一个让抖音的机器算法认为好的内容”。
更准确说是“怎样通过内容激发用户行为,进而让算法识别到数据,给内容匹配更多流量”,创作者为此苦心钻研。
一位北京MCN老板分享,抖音短视频讲究“三幕”原则:开篇用“黄金三秒”抓人眼球,中间冲突不断让用户停留,结尾要么悬念、要么反转、要么令人大呼过瘾,引导用户点赞。
他们精心设计每一帧,和编剧强调“文本能少一个字是一个字”、“视频能少一秒是一秒”。因为时长影响完播率,经验来看完播率、点赞数是决定内容分发的有效指标。
“千万不要小看1%或2%。它可能导致这条视频只推荐给一万人,而不是十万人。”
“只要数据不好就焦虑。”慕容继承是新动传媒CEO,旗下祝晓晗账号拥有4500万粉丝。巨量粉丝攫取之路遍布坎坷。增加人物线是走出阴霾的途径之一。
“多一个角色就多了一些冲突,以前是老爸和闺女,现在是老爸和老妈,老妈和闺女,闺女和老爸。可创作空间变大了。”他认为MCN核心竞争力是持续内容创作能力。
很多抖音短视频达人是演绎大于真实,用抖音前员工的说法:“快手在记录生活,抖音在策划生活。”
算法驱动的平台,哪怕零粉丝,只要有爆款炸出来,就会迎来猛烈涨粉。它顺应人性、充满爽感,但这也是最难受的——粉丝数不等同于商业价值。 “说白了都是给平台打工。”一位MCN老板说。
由算法支配的恐惧步步紧跟。“没有一个达人不焦虑的。”即使拥有强人设、粉丝量3000多万的毛毛姐,每当点赞量不到一百万,也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觉得自己要凉了”、“好不容易站起来,万一不行了怎么办?”
抖音加速使人辉煌,也加速使人坠落。今年越来越多人说,刷到毛毛姐的视频变少了。
现在他的点赞大多只有几十万,甚至十几万。而像他这样火了一年多,在抖音已是稀有物种。对更普遍玩家而言,来得快、去得也快,“起伏就三个月”。
“抖音真的是大起大落。说红就红,说过气就过气。红的时候一夜之间全是他,过一阵就消失了。”一位广州MCN内容负责人说。“在平台面前,网红都不值一提,”另一位北京MCN内容负责人说,“网红是正儿八经向‘死’而生。”
创作者为了迎合算法完播率,视频节奏越来越快、时长越来越短。一条视频爆了,无数人跟风翻拍。
为了赚流量,有MCN不惜让十几个网红同时拍一个脚本。随之而来的是同质化泛滥和审美疲劳。
上述广州人士把一些人做抖音的心态比喻成“上赌博机”,盼望一朝被算法选中,爆红、暴富,又浮躁又投机。价值观输出成为奢望——这些都让单个原生达人难以掀起巨大风浪。
“你看现在最火最火的视频不超过10秒。”薛老湿说。
“过气的场景在我这已经演练一万遍了。”面对无法撼动的推荐机制,毛毛姐比以往平和,还安慰身边人:“不要去操心你控制不了的。”他设想,要是哪天彻底没人看他视频了:“就做回一个普通老百姓,又能怎么样呢?”
“抖音的推荐机制决定了,永远拥抱新入局者。”一位广州MCN老板说。
MCN中,一个重要分支是以前做微博、公众号的老板,他们带着流量思维迁徙而来。他听过无数这类老板吐槽,抖音是做过最累的行业,“每天都是新的开始”。
不同内容风潮如浪花此起彼伏。剧情号以前,技术流、颜值、唱跳、搞笑等,都催生了头部网红,形成全网风潮,但每一种内容风潮兴起后又总会归于平静。
毛毛姐在2017年下载过抖音,“一刷全是花花绿绿、晃来晃去的,真是看不懂”。他马上把App删了,2018年才下回来,这从侧面应证了抖音的大众化。
而帮抖音起步的技术流,早已隐没进生态角落。
刘多说,一些20-30万粉丝的技术流博主,还会跑到老达人群控诉:“我是你们当时跪着求着要来的,现在你们不管我了。”作为抖音元老,薛老湿粉丝200多万。
他的态度是,抖音不再是他们的玩具,它是“主流文化的催化剂”,是“资本的工具”,他呼吁创作者不要忘记表达的初心。
抖音早早把帮达人变现提上日程:2018年5月启动非标广告,6月启动标准广告星图系统(可在线接广告主发布的推广任务),并上线电商。
抖音企图把分散在各个角落的经纪业务抓到自己手中,字节是广告变现一把好手,抖音很快继承过来。
“大家对抖音都是又爱又恨的。”另一位广州MCN老板说。爱抖音因为流量大,容易广告变现。恨抖音在于,它把流量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抖音不依赖任何网红,既是幸运,也是悲哀。幸运是抖音可以不依靠任何人做得很好。悲哀的是,大家看不到希望,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兵就是达人。”
“更夸张说抖音没有网红。你的粉丝根本不是你的粉丝,是抖音的粉丝。你的流量也不是你的流量,是抖音的流量。所有流量都是张一鸣的。”一位北京MCN老板说。
在抖音,3000万、4000万粉丝只能叫“粉丝量头部”,和实际头部地位完全不匹配。
2019年抖音大举做直播,上述现象更显著。淘宝直播有薇娅、李佳琦,快手有辛巴,他们是平台绝对头部。而抖音直播,“粉丝量2000万的达人,直播间在看人数可能只有1000”,上述老板称。
“你必须要让达人有足够的话语权。如果你的达人不强势,我认为这个平台是不健康的,变成你自己去玩。即使平台有安全感,也是很短暂的安全感。”另一位MCN人士说。
抖音一度想过帮达人艺人化,将潜力股捧上综艺。可惜没成功。讽刺的是,一些在抖音没火起来的人,在外面意外走红。
一位运营说,火箭少女101段奥娟曾在抖音穿校服唱歌,杨超越、费启鸣、摩登兄弟也都是运营维护的对象,“我们把他们当成做不起来的达人。”
他记得当年有同事和摩登兄弟吃烤鸭,没想到两年后,再次到附近餐馆,抬起头,央视一套放着摩登兄弟。他们摇身变成明星,光彩照人、火遍全国,只是和抖音无关。
“不能只在抖音火”是MCN老板的新共识,不少人跨平台寻求安全感。白水说,要在流量高峰去做破圈的事。
五月决定发力小红书、B站和视频号,努力让团队跳脱抖音思维,继而降低单平台依赖。抖音直播曾以流量扶持诱惑MCN签独家,上述北京MCN老板没有答应,“为啥要在一家绑死呢?”
今年,MCN狂热已然冷却许多。 2019年一拨人奋不顾身冲进来,但拍短视频成本高,很多玩家入不敷出,真正挣到钱的不多;2020年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行业理性和冷静了。
“从投机式地批量做号转向精品化账号。”上述广州内容负责人说。
“核心就是因为抖音懂人性。它是利用创作者想火、想红、想要流量的心理激发他们创作。同时把这个流量卖给广告主,”上述北京内容负责人说道,“创作者是平台繁荣的燃料。”
2020年9月,在刚过去的创作者大会上,张楠表示,过去一年,超过2200万人在抖音合计收入超过417亿元。未来一年,他们要让创作者收入达到800亿。
抖音用豪放的流量和金钱刺激创作者,在欲望驱使下,大家卯足了劲卖命工作。他们亲手投递一波又一波内容,喂饱了算法,壮大了抖音流量帝国。
在算法主宰的世界,就像抖音不那么需要灵魂人物,它也不需要头号玩家。
“但是你要让人误以为可以成为头部,成为大腕,”一位前抖音人士称,“平台必须给人这样的梦想。”
七、更功利主义
抖音和快手的交战史,是一个后来者凶猛的经典案例。
“我们压力太大了,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全方面被抖音超越的感觉。”一位快手人士告诉我。一名抖音较早员工站在现在回想说:“我们定义做成快手那样子估计早死了。”
比对两大短视频平台的生态会发现,抖音更像工业社会,快手更像乡土社会。
在用户侧,抖音界面是全屏上下滑,机器推荐痕迹重;快手以前是双列陈设,更多选择权交给用户。
知情人士称,快手“关注页”流量占比有近40%,达人和用户粘性强。
在创作者侧,抖音强运营、重视MCN、工会这些机构化组织;快手社区氛围友好,依靠自下而上自然生长,长出几大家族,更具江湖气——结果是,抖音牢牢握住流量命脉,快手权力分散。
看起来,快手生态更温情,而抖音冷漠。但在如狼似虎的商业社会,它影响了广告变现效率。
“抖音的流量大部分是官方控制,我把我的利益最大化,”一位广告业人士说,快手痛苦在于,“(流量)掌握在各方势力手里,治理起来太难了,各种山头摆不平。往往就是多方博弈的过程。”
今年创作者大会,抖音公布6亿日活(含火山版),震惊互联网行业。如果公布另一组数据,涨势更为惊人。
腾讯新闻《潜望》独家获悉,抖音今年广告营收目标超过900亿元。
短视频平台变现来源主要是广告和直播打赏。
2018年以来,抖音广告高歌猛进——150亿(2018年),600亿(2019年),目标900亿(2020年),同比增速50%。而快手,去年广告完成130亿上下,今年目标约400亿,仍难望其项背。
再来看直播。这原本是快手大本营,2019年抖音组建直播中台,大量引进工会。
“工会要完成任务,逼着这些人工作时长越来越长,不完成任务不能下播。”知情人士在2020年8月告诉我,今年春节后,作为后起之秀的抖音直播,单日营收稳定过亿,而快手直播却在1亿上下波动。
“快手强调人人平等,但是遇到一个组织化力量去对抗的时候,有些被动。”
他依现有数字估算,抖音2020年国内营收或能达1300-1500亿左右。这也意味着,抖音是字节跳动头号印钞机。
快手偏社区,抖音更具媒体属性。 “抖音所有的优化都是朝着DAU和收入去平衡,”一位字节中层将两款应用比喻成两个国家,“抖音更关注GDP(国内生产总值),快手更关注人均收入。”他评价快手具有普惠价值观,而抖音“是公司赚钱的机器”。
上升到哲学语境,“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是影响世界的不同流派。一个看重物尽其用、效率最大化,一个追寻众生平等。 抖音始终贯穿前者,快手起步于后者。
这从他们的slogan可窥见一斑,抖音呼吁“记录美好生活”,快手拥护的是“拥抱每一种生活”。
抖音想过再次修正slogan,2019年他们到访薛老湿家,提出一个疑惑。用户下沉以后,平台出现大量劣质内容,审核负担过重。 抖音思考,是否应该转而鼓励“让真正的创作者浮出水面”。
另一个事例是针对广告业务的态度,“快手强调用户愉悦感,认为广告是破坏用户体验的。但是字节从一开始认为,广告也是信息的一部分,和它的信息分发逻辑一脉相承。”上述广告业人士说。
底层认知差别,是影响今日抖音和快手商业化格局的原因之一。
两种价值观并无对错,只是路径不同。但商业世界异常冷酷,在遭遇打击后,快手越来越抖音化。
第三方机构极光的监控数据显示,2020年9月以来,抖音(含极速版、火山版)平均日活4.08亿,快手(含极速版)2.37亿。
八、算法黑盒
现在,在中国街头巷陌,你会随时看到盯着手机屏傻笑的人。
每天,有6亿人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打开抖音(注:官方统计口径)。他们来自大城市、来自小镇、来自乡村,他们平均在上面耗费近两个小时。
据极光的数据,抖音2020年9月以来日均使用时长是:抖音App6.3亿小时、极速版0.71亿小时、火山版0.35亿小时。转换过来,抖音单日烧掉全国人民441.6亿分钟——将近9万年。
时间熔炉之火熊熊燃烧。
外界把抖音比作“杀时间利器”。 “它很无聊,无聊的时候会用它,”一位字节在职员工说,“实在没事我会刷一会儿,会上瘾。”为了摆脱负面舆论,抖音把时间上限放宽至15分钟,并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抖音是沉浸式的,像个游戏。”一位离职员工说。
全国分布来看,素有“南抖音、北快手”之称。 “抖音下沉渗透率高于我们的想象。”一位接近抖音人士说。他从内部看到另一个有趣图谱:高校越好,抖音渗透率越低,B站渗透率越高。
更有意思的是,掌门人张一鸣极力宣扬“延迟满足感”,而“他的公司开发了及时反馈到极致的App”,某位互联网从业者笑谈道。
抖音2016-2020年日活跃用户数增势,仅统计抖音App
在抖音的工业帝国里,机密而严明的规则无处不在。
抖音审核规则是全平台里最严苛之一,除机器审核,人工审核团队过万人。两名运营告诉我,视频里不能抽烟,不能露出打底裤,没有水不能穿比基尼,甚至精确了“比基尼露出来多少比例”。
如果视频要带货,“是不可以有任何未成年人出镜的”。一位创作者说,他曾因视频背景出现玛丽莲梦露捂裙子的经典海报,遭封禁。
几乎每个在平台里谋生的人,都经历过匪夷所思的时刻。
一位财经创作者说,有时流量莫名地差,他们会找运营“捞视频”,“这个视频被关小黑屋。”他说。
对方会告知他,视频“可以捞”或“不可以捞”,有时表示“存在大量违规内容”,但不会解释原因和具体违规事项。
他还发现,抖音有可能存在微妙的商业禁忌。
当发表评论涉及某些品牌商,你以为你的评论发出去了,拿另一个手机看,那条信息实际消失。他判断大概率遭到了拦截,仅发布者或少数私域可见。
“名义上是审核,但不知道触犯了什么逻辑,也不知道审核原则到底是什么。”他用“抖音的密语”来形容:“你不知道哪些品牌商的名字是不能提的,也不知道哪些话是红线。”
创作者大会前,抖音官方人员询问某剧情创作者,我们最能解决你什么痛点? “你们把审核机制给我整明白。每次都撞大运,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你们审核不过,我今天活就白干了。”他答。
多位创作者和MCN老板比喻,抖音是“不可琢磨的算法黑盒”。
迷惑不止于外。 “也非常非常困扰我们。”在抖音工作过两年的运营,表达了相似的感受。
极端存在两种情形:一些时候是,用户点赞等后台数据都表现良好,但就是得不到更多推荐;一些时候是,明明视频有违规,却在持续地被推荐着。他们只能不停上报给算法部门。“比较明显的会立即处理,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可能过去也就过去了。”
上述运营说,你知道盒子在高效运转,你能粗浅描摹轮廓,但谁也不知道里面精密的结构和零部件。更何况,五花八门的算法权重调整实验密集展开,这个庞然大物每天都在变化。
见证抖音崛起的早期员工,也描绘了颇为魔幻的场景:算法工程师就坐他身后,每当内容推荐莫名其妙,他就扭过头质问他,算法工程师只是无奈撇撇嘴:“我也不知道啊。”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推荐算法极其复杂。
它根据大量特征刻画用户行为——比如这条视频看完没看完、看到第一秒还是第五秒、在第三秒点的赞还是在第五秒点的赞、点了一下赞还是五百下赞……每个特征维度都有非常多可能的取值,总特征数在百亿到千亿规模。
这些特征的不同组合方式更是天文数字,事实上,机器学习模型一旦跑起来,“没有人能理解”。
算法看上去无所不能:既能调控网红的成名和陨落,又能吸引用户沉迷,还能催生资本变现。
“内部很多人实际上在和算法做对抗。有些部门看起来挺有权限的,但是在算法面前,算法最大。”一位MCN人士举例说,在抖音,做商业化直播需要开白名单。
比如,具有美白功效的商品,必须具备美白特证,才能正常开播。但经常情况是,开了白名单,拿着美白特证,某些词依然会触碰内容审核关键词,他们被平台警告,甚至被踢下线。
对此,商业化部门也无奈,和他们一起“抱怨抖音的算法问题”。
这个故事里,抖音从温情社区渐变为强势商业系统。人们一面享受着效率和财富,一面体会着随之而来的冷漠和无情。
一位科技观察者用“赛博朋克”来形容——抖音世界娱乐至上、霓虹闪烁,科技力量日益强大,人们煞费苦心,知道得却是皮毛。
花四年时间,抖音改变了字节跳动的命运,为之拿到跻身互联网一梯队的门票。
据极光,抖音(含极速、火山版)日活目前只低于微信,排名中国移动互联网第二。字节跳动估值千亿以上美金,随着蚂蚁金服近期挂牌,它将晋升为全球最大未上市独角兽。
但抖音没有停止恐惧。 “我们不知道抖音什么时候会死。”向眯记忆中,张楠经常对内谈及此,她认为抖音必须提供有价值、有用的内容,尽最大可能延长生命周期。
如今,抖音早已不再是“抖音”。它不是音乐短视频社区,甚至也不是短视频平台,最新版App悄然从“抖音短视频”更名“抖音”。
它已成为集视频、直播、电商、社交、本地生活等于一身的“怪兽”,并且试图长出更多臂膀。
管理层在2019年提出“演化”,探究抖音究竟往哪去。是内容平台?还是社交平台?内部观点分裂成两种。
前者认为应延展内容平台方向,将爱优腾和新闻媒体覆盖的PGC内容做起来;后者认为要抢占社交。两位抖音人士说,它在两者间有些徘徊。
“你要知道,字节现在已经影响的是一个社会,”一位字节中高层说,“这里面遇到最严峻的问题,字节虽然做得很大,提速很高,市值很高,但它和AT有个最本质的区别——它不具备社会价值。腾讯提供沟通,阿里是交易的基础设施,抖音提供啥了?”
这种焦虑烧到了公司最高层会议上。知情人士告诉我,从去年开始,张一鸣把“社会价值”列为高管会的首项固定议题。
字节跳动是中国少数没有年会的互联网公司。
2019年初,赶超快手后的第一个除夕,抖音有三十来人留守过年。公司准备好年夜饭,张一鸣出面犒劳团队。
这位很少表扬团队的创始人,和在座诸位打招呼。理所当然地,他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举起酒杯,只是拿一摞钱来,给每人发了两千块红包。
“抖音摩天大楼不可能靠一个工程师建起来,可能一鸣也不清楚,最终每行代码起什么作用。”一位员工说。
(文中刘多、向眯为化名。)








![《金瓶梅》崇祯版等多版本合集(包括名家点评本)[Epub.Mobi.PDF]推荐-老王博客](https://www.9im.cn/wp-content/uploads/2021/05/444444443.jpg)

![表情[liulei]-老王博客](https://www.9im.cn/wp-content/themes/zibll5.73/img/smilies/liulei.gif) 我也不是骗子,我以前有QQ号,但是无法登录了,申诉也不给我,真的没办法,有没有人愿意帮这个忙,万分感谢。
我也不是骗子,我以前有QQ号,但是无法登录了,申诉也不给我,真的没办法,有没有人愿意帮这个忙,万分感谢。![表情[fadai]-老王博客](https://www.9im.cn/wp-content/themes/zibll5.73/img/smilies/fadai.gif)





请登录后发表评论
注册
社交帐号登录